随笔
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白痴》作为文化制品与精神分析视域中的解构对象
该文本基于2025年在圣彼得堡Mikhail Shemyakin中心举行的会议上提交的报告
《3D白痴》项目创作声明
2022年,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以政治禁令为名,事实上被排除在西方文化流通之外。这一举动并非单纯的审查,而是一场试图抹除曾被奉为“世界文学经典”的整个思想层的行动。
《3D白痴》项目并非以论辩回应这一禁令,而是以形式作出回应。我不再捍卫文本,而是提出它的转化:这本书不再被阅读——它被观看。
我借助德里达(Jacques Derrida)的解构方法与拉康(Jacques Lacan)的结构精神分析逻辑,将禁令视为一种形式生成的行为。正如在心理结构中,乱伦禁忌所催生的并非虚空,而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秩序;同样,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化禁令所引发的,也并非消失,而是一本新形态之书的诞生。
《白痴》是一部关于神圣之善的小说——这种善被世界误解、拒绝。在禁令之下,这本书本身便成了“白痴”:一位无人愿听的真理承载者。它的“疯狂”,正在于拒绝服从文化沉默的逻辑。
在本项目中,小说的每一页都依照折纸原理被折叠成锐利的形态。文字依然可见,却不可读——意义被姿态所取代。读者让位于观者,线性的书页序列转化为一种空间性的展开。书名被赋予“3D”前缀:这不仅指物理的体积,更指向书籍存在的三重维度——历史的(陀思妥耶夫斯基)、物质的(纸张、形态)与当代的(作为见证者的艺术家)。
《3D白痴》宣告:艺术无法被禁止。它只能被逼迫改变。而正是在这种改变之中,蕴藏着它的力量。
3D白痴项目:当禁令将文本变成形式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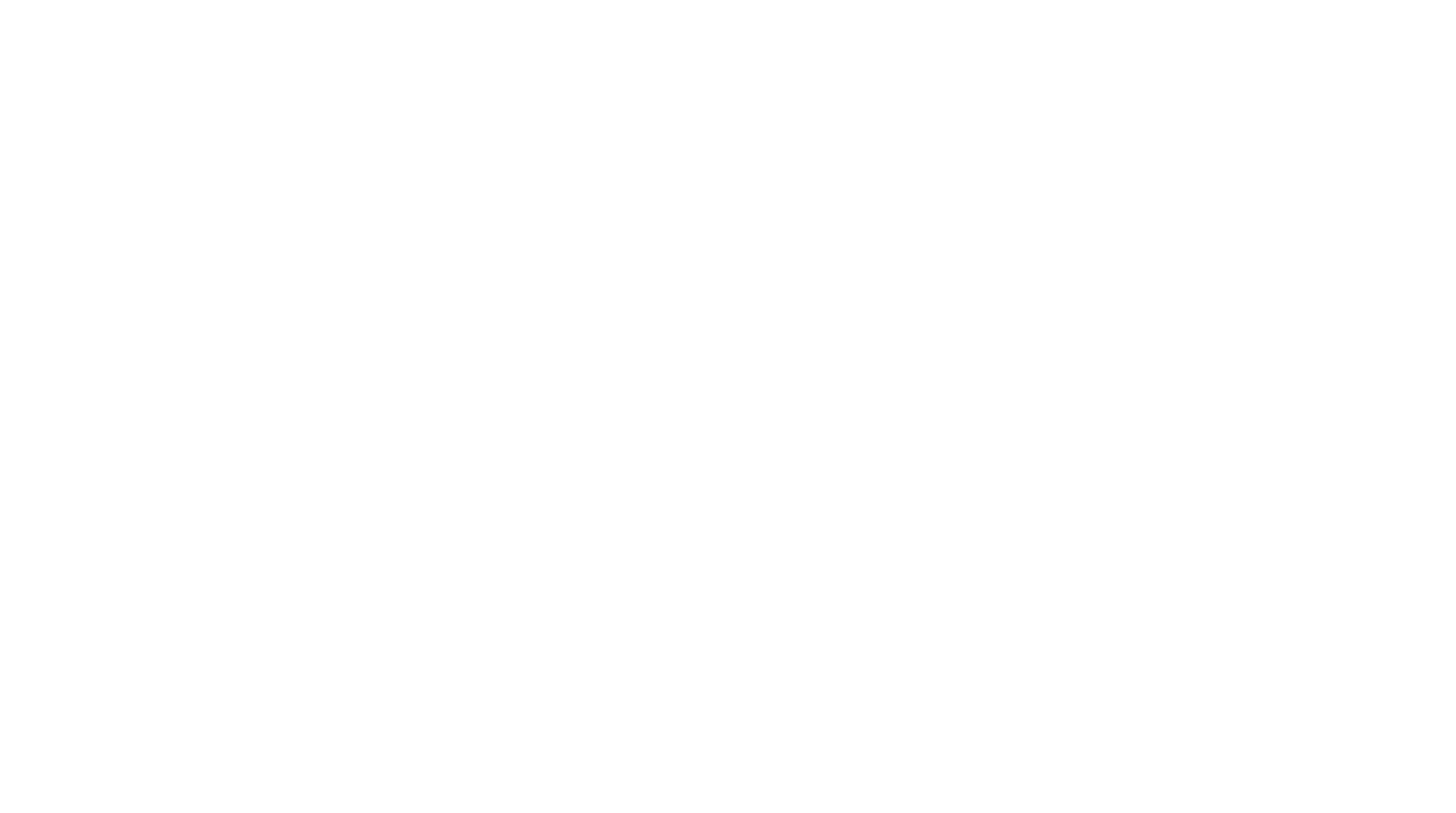
1. 对象进入后现代文化场域的轨迹
艺术作品《3D白痴》是一本被转入新维度的书。在当代性与文化政治变迁的作用下,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助后现代主义特有的方法,获得了新的形态。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否定——但并非摧毁,而是转化。它使我们得以揭示那些看似“习以为常”、“众所周知”或“不言自明”之物(即刻板印象)内部的隐秘结构。
这种重新思考的关键工具之一,便是雅克·德里达的解构。解构旨在动摇固定的意义,揭示维系对象刻板整体性的那些要素。当这样一个对象——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——被置于新的语境中(在此即文化禁令的情境),其结构便发生变形,并暴露出自身的支撑点。
雅克·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有助于勾勒出这一转化的可能轨迹。若将文化对象视为一个依循特定法则形成的主体,那么它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便是可预测的——前提是这种作用符合精神分析机制的逻辑。在我们的案例中,这一交汇点正是禁令的逻辑。
2022年,西方文化机构事实上宣布禁止俄罗斯经典作品,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。在拉康理论中,对乱伦对象(母亲)的禁令不仅是一种限制,更是一种形式生成行为:它产生“匮乏”(manque),进而启动象征性创造与心理结构复杂化的过程。同样,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亦可被解读为一种邀请——邀请我们创造一种新的、更复杂的形态,而非将其抹除。
2. 作为文化建构物的书籍结构分析
对俄罗斯文化的禁令,尽管短暂且非正式,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应——与其说是政治性的,不如说是审美性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,尤其是《白痴》,之所以成为焦点,正因它们不仅是文学,更是一种文化刻板印象:“艰深”、“阴郁”、“深刻”、“难以理解”。这种刻板印象使其成为解构的理想对象:它既稳固,又脆弱。
我们可以将“书”视为一个由以下要素构成的建构物:
– 封面
– 书页
– 书名
– 作为符号系统的文本
– 作为意义传递的内容
– 作者(作为文化形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)
– 读者
– 刻板印象(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书”作为一种文化符码)
传统上,读者与文本展开对话:认同、争辩、诠释。但正是读者将所有其他要素联结为一个整体。一旦抽离读者,书便不再作为文化对象而存在。
3.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中的禁令逻辑
在精神分析中,禁令并非简单的禁止,而是一种文化律法,它剥夺主体对欲望对象(经典案例中即母亲)的直接通路。这种丧失催生“匮乏”,而匮乏正是象征性创造的驱动力。主体开始寻找替代物,构建隐喻,使自身内在结构日益复杂。
同样,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制造了一种文化匮乏。但对象并未因此消失,而是趋向转化——它在寻求新的存在方式。这正是解构过程的起点。
4. 读者的拆解与匮乏的生成
若禁令针对俄罗斯文化,其直接对象便是读者——作为能够接收并传递这一文化符码的当代人。失去读者,书便丧失其功能。解构由此从拆解读者这一要素开始。
在精神分析逻辑中,对象的丧失不会导致虚空,而是启动重构过程。建构内部的诸要素开始转换功能、占据新位置、形成新的联结。
5. “读者”对象的结构
读者所面对的文本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:
– 想象界(Imaginary):作为对世界的描述,
– 象征界(Symbolic):作为意义的传递。
相应地,读者的功能亦具双重性:他既阅读(处理意义),也观看(感知形式)。这种双重性可表述为两个对象的分裂:读者与观者。
6. 对象间功能的重新分配
当阅读功能被废除,观者便走向前台。他不再揭示意义,而是感知形式。内容的位置被艺术家的姿态所取代——这是由禁令所物质化的情动(affect)。这一姿态蕴含抵抗的能量,却非破坏之力:在拉康逻辑中,受律法规约的情动并非指向禁令源头的毁灭,而是导向自身结构的复杂化。
重要的是:接受律法不等于认同律法。艺术家并非为禁令辩护,而是将其纳入自身系统,从而从内部创造新形式。这正是后现代回应的精髓:艺术无法被禁止——它总会找到回应的方式。
7. 新书结构的材料组装
解构的结果催生了新对象:
– 艺术家的姿态(以情动形式呈现),
– 观者。
以下要素得以保留:
– 带有文字的书页,
– 书名《白痴》,
– 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。
作者的功能部分转移至艺术家: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盟友与旁观者,而非意义的唯一源头。封面失去意义——因为观者不像读者那样“进入”书籍,而是将其整体感知。书页的线性序列不再必要:书可被拆解,以便一次性被完整看见。
8. 作为形式生成要素的刻板能指
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获得了字面意义:书成为物理上被折叠之物。“艰深”(slozhnaya)与“折叠”(slozhen-naya)在发音上的相似性开启了一个新的能指。这一滑移引导了艺术技法的选择——折纸(origami),在此技法中,纸张被折叠为新形态,同时保留原始材料的可识别性。
9. 通过能指实现情动的形式生成
由禁令引发的情动,常被联想为尖锐、刺痛、具攻击性之物。折纸技法使书中的每一页都转化为尖锐的形态——既具威胁性,又显脆弱。文字依然可见,却不可读:意义被形式所取代。这正是禁令条件下对话之不可能性的视觉化呈现。
10. 为观者而存在的书:形式的阅读
新书不再存在于线性维度,而存在于空间维度。所有被折成尖锐形态的书页,依次排列于两个平面上——如同一件装置的展开图。每一页都将目光引向其尖端,在此处,物质性过渡至象征性:艺术家的姿态正凝聚于此。
11. 书名的转化
书名《白痴》获得前缀 3D——这不仅指涉体积。《3D白痴》意指:
– “立方体中的白痴”:对试图“封装”并隔离俄罗斯文化的回应;
– 书籍在三维空间中的字面具身化;
– 新书的三重维度:
结语
《3D白痴》不仅是对经典的重新诠释,更是一次通过形式实现的文化抵抗。禁令并未摧毁书籍——它迫使书籍重生。在新构型中,读者让位于观者,意义让位于形式,线性让位于空间。但最重要的是:书依然存在——不再作为文本,而是作为姿态、挑战、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对象。
艺术作品《3D白痴》是一本被转入新维度的书。在当代性与文化政治变迁的作用下,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借助后现代主义特有的方法,获得了新的形态。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否定——但并非摧毁,而是转化。它使我们得以揭示那些看似“习以为常”、“众所周知”或“不言自明”之物(即刻板印象)内部的隐秘结构。
这种重新思考的关键工具之一,便是雅克·德里达的解构。解构旨在动摇固定的意义,揭示维系对象刻板整体性的那些要素。当这样一个对象——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——被置于新的语境中(在此即文化禁令的情境),其结构便发生变形,并暴露出自身的支撑点。
雅克·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有助于勾勒出这一转化的可能轨迹。若将文化对象视为一个依循特定法则形成的主体,那么它对外部作用的反应便是可预测的——前提是这种作用符合精神分析机制的逻辑。在我们的案例中,这一交汇点正是禁令的逻辑。
2022年,西方文化机构事实上宣布禁止俄罗斯经典作品,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。在拉康理论中,对乱伦对象(母亲)的禁令不仅是一种限制,更是一种形式生成行为:它产生“匮乏”(manque),进而启动象征性创造与心理结构复杂化的过程。同样,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亦可被解读为一种邀请——邀请我们创造一种新的、更复杂的形态,而非将其抹除。
2. 作为文化建构物的书籍结构分析
对俄罗斯文化的禁令,尽管短暂且非正式,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应——与其说是政治性的,不如说是审美性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,尤其是《白痴》,之所以成为焦点,正因它们不仅是文学,更是一种文化刻板印象:“艰深”、“阴郁”、“深刻”、“难以理解”。这种刻板印象使其成为解构的理想对象:它既稳固,又脆弱。
我们可以将“书”视为一个由以下要素构成的建构物:
– 封面
– 书页
– 书名
– 作为符号系统的文本
– 作为意义传递的内容
– 作者(作为文化形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)
– 读者
– 刻板印象(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书”作为一种文化符码)
传统上,读者与文本展开对话:认同、争辩、诠释。但正是读者将所有其他要素联结为一个整体。一旦抽离读者,书便不再作为文化对象而存在。
3.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中的禁令逻辑
在精神分析中,禁令并非简单的禁止,而是一种文化律法,它剥夺主体对欲望对象(经典案例中即母亲)的直接通路。这种丧失催生“匮乏”,而匮乏正是象征性创造的驱动力。主体开始寻找替代物,构建隐喻,使自身内在结构日益复杂。
同样,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禁令制造了一种文化匮乏。但对象并未因此消失,而是趋向转化——它在寻求新的存在方式。这正是解构过程的起点。
4. 读者的拆解与匮乏的生成
若禁令针对俄罗斯文化,其直接对象便是读者——作为能够接收并传递这一文化符码的当代人。失去读者,书便丧失其功能。解构由此从拆解读者这一要素开始。
在精神分析逻辑中,对象的丧失不会导致虚空,而是启动重构过程。建构内部的诸要素开始转换功能、占据新位置、形成新的联结。
5. “读者”对象的结构
读者所面对的文本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:
– 想象界(Imaginary):作为对世界的描述,
– 象征界(Symbolic):作为意义的传递。
相应地,读者的功能亦具双重性:他既阅读(处理意义),也观看(感知形式)。这种双重性可表述为两个对象的分裂:读者与观者。
6. 对象间功能的重新分配
当阅读功能被废除,观者便走向前台。他不再揭示意义,而是感知形式。内容的位置被艺术家的姿态所取代——这是由禁令所物质化的情动(affect)。这一姿态蕴含抵抗的能量,却非破坏之力:在拉康逻辑中,受律法规约的情动并非指向禁令源头的毁灭,而是导向自身结构的复杂化。
重要的是:接受律法不等于认同律法。艺术家并非为禁令辩护,而是将其纳入自身系统,从而从内部创造新形式。这正是后现代回应的精髓:艺术无法被禁止——它总会找到回应的方式。
7. 新书结构的材料组装
解构的结果催生了新对象:
– 艺术家的姿态(以情动形式呈现),
– 观者。
以下要素得以保留:
– 带有文字的书页,
– 书名《白痴》,
– 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。
作者的功能部分转移至艺术家: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盟友与旁观者,而非意义的唯一源头。封面失去意义——因为观者不像读者那样“进入”书籍,而是将其整体感知。书页的线性序列不再必要:书可被拆解,以便一次性被完整看见。
8. 作为形式生成要素的刻板能指
“艰深之书”的刻板印象获得了字面意义:书成为物理上被折叠之物。“艰深”(slozhnaya)与“折叠”(slozhen-naya)在发音上的相似性开启了一个新的能指。这一滑移引导了艺术技法的选择——折纸(origami),在此技法中,纸张被折叠为新形态,同时保留原始材料的可识别性。
9. 通过能指实现情动的形式生成
由禁令引发的情动,常被联想为尖锐、刺痛、具攻击性之物。折纸技法使书中的每一页都转化为尖锐的形态——既具威胁性,又显脆弱。文字依然可见,却不可读:意义被形式所取代。这正是禁令条件下对话之不可能性的视觉化呈现。
10. 为观者而存在的书:形式的阅读
新书不再存在于线性维度,而存在于空间维度。所有被折成尖锐形态的书页,依次排列于两个平面上——如同一件装置的展开图。每一页都将目光引向其尖端,在此处,物质性过渡至象征性:艺术家的姿态正凝聚于此。
11. 书名的转化
书名《白痴》获得前缀 3D——这不仅指涉体积。《3D白痴》意指:
– “立方体中的白痴”:对试图“封装”并隔离俄罗斯文化的回应;
– 书籍在三维空间中的字面具身化;
– 新书的三重维度:
- 艺术家的维度(当代性),
- 物质的维度(纸张、形式、物体),
- 作家的维度(历史性、传统)。
结语
《3D白痴》不仅是对经典的重新诠释,更是一次通过形式实现的文化抵抗。禁令并未摧毁书籍——它迫使书籍重生。在新构型中,读者让位于观者,意义让位于形式,线性让位于空间。但最重要的是:书依然存在——不再作为文本,而是作为姿态、挑战、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对象。
